儿童电影三国志
2008年04月16日 15:10阅读次数:1056
环顾当今世界影坛,能进入视线之内的儿童影片,似乎只集中于两个曾经对立的国家——美国与伊朗。作为全球电影的龙头老大,好莱坞每年都会炮制出数部儿童题材的洪片巨制
之路,影片的后半部分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记录片。而这样坚韧和勇敢在孩子们的身上总是表现得让人肝肠寸断,《永恒的爱》中不断寻找母亲形象的男孩;《手足情深》里被人贩子拆散的一双孤儿兄妹;《天堂的颜色》那只能用耳朵和双手感受天籁之音,却被父亲抛弃的盲童;《醉马时刻》则讲述了失却父母的库德族孩子肩负起生存的责任,往返于地雷和游击队密布的山区走私,而那条路,冷得连骡子都需灌醉酒才能越过边界;而阿巴斯更在最新的《ABC在非洲》中,用DV镜头记录了乌干达数千名孤儿,他们被艾滋和内战夺走了父母,却仍在困苦黑暗中寻找生命的欢乐,在死亡和疾病的笼罩下坚韧的存在。
伊朗电影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视觉风格,从民族境遇出发,将书写日常生活的电影带给观众,在电影回归本身的同时,突破了民族和文化的界线,试图重归冲刷人类身体的那条生命河流,反映稍纵即逝的平凡中蕴涵的某种永恒,透过儿童的目光对人类的生存重新做了一次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和审视。它引领我们再度进入那个电影和生命交错摩擦的天地,沉淀心灵,无语凝咽。
中国儿童片:童年成长物语
儿童电影三国志之中国篇
当《哈里·波特》那个戴着大眼镜手持魔棍的瘦弱男孩旋风一样迅速刮遍全球,把孩子们甚至一家老少重新带回影院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已经多久没有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影而欢笑叹息了?
70年代出生的人依然能够流利地哼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插曲来自50年代的优秀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历经半个世纪传唱至今,优美舒缓的旋律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荡过成长之河,然后被深深烙进记忆丛林的年轮。而巧送《鸡毛信》的机智海娃,与《小铃铛》同台“竞技”的石满和马佳,被土家族男孩安吉斯演活的《小兵张嘎》,潘东子和椿伢子心中那颗《闪闪的红星》,眼睛若井水般清亮的英子在林海音与吴贻弓的《城南旧事》虚实相构中顾盼……岁月更迭流转,银幕上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曾辉映了整个童年的快乐,窘迫匮乏的生活中我们却有着异常丰富的记忆宝藏。
然而,小海娃蔡元元连《大辫子的诱惑》都拍过了,石满、张嘎子、潘东子这些银幕上的孩子也早已跨过不惑之年,进入21世纪的孩子们能够在六.一看到的儿童电影,翻来覆去还是那些他们的父辈业已谙习N遍的经典:《三毛流浪记》、《红象》、《苗苗》、《四个小伙伴》、《泉水叮咚》、《月光下的小屋》、《自古英雄出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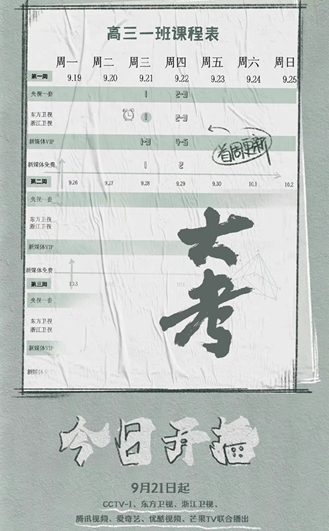





还没有人评论哦,赶紧抢一个沙发吧!